入夜,,城隍廟,。
謝昭打從進入城隍廟便像只趴了窩的鵪鶉,,她找到了一個相對干爽潔凈的角落,,然后便靠著柱子半點沒有講究的坐下,旋即整個人窩著蜷縮在裹緊的大氅中,,帶著氅帽一動不動,。
凌或是行動派,話少但是能干,。
其實方才路上他便已然發(fā)現(xiàn)與薄熄共乘一騎的謝昭像只蔫吧缺水的狗尾巴花似得,,老實安靜的可疑。
此時見狀更是不難聯(lián)想到她必是因先前在林中動過手,,導(dǎo)致那身舊傷舊毒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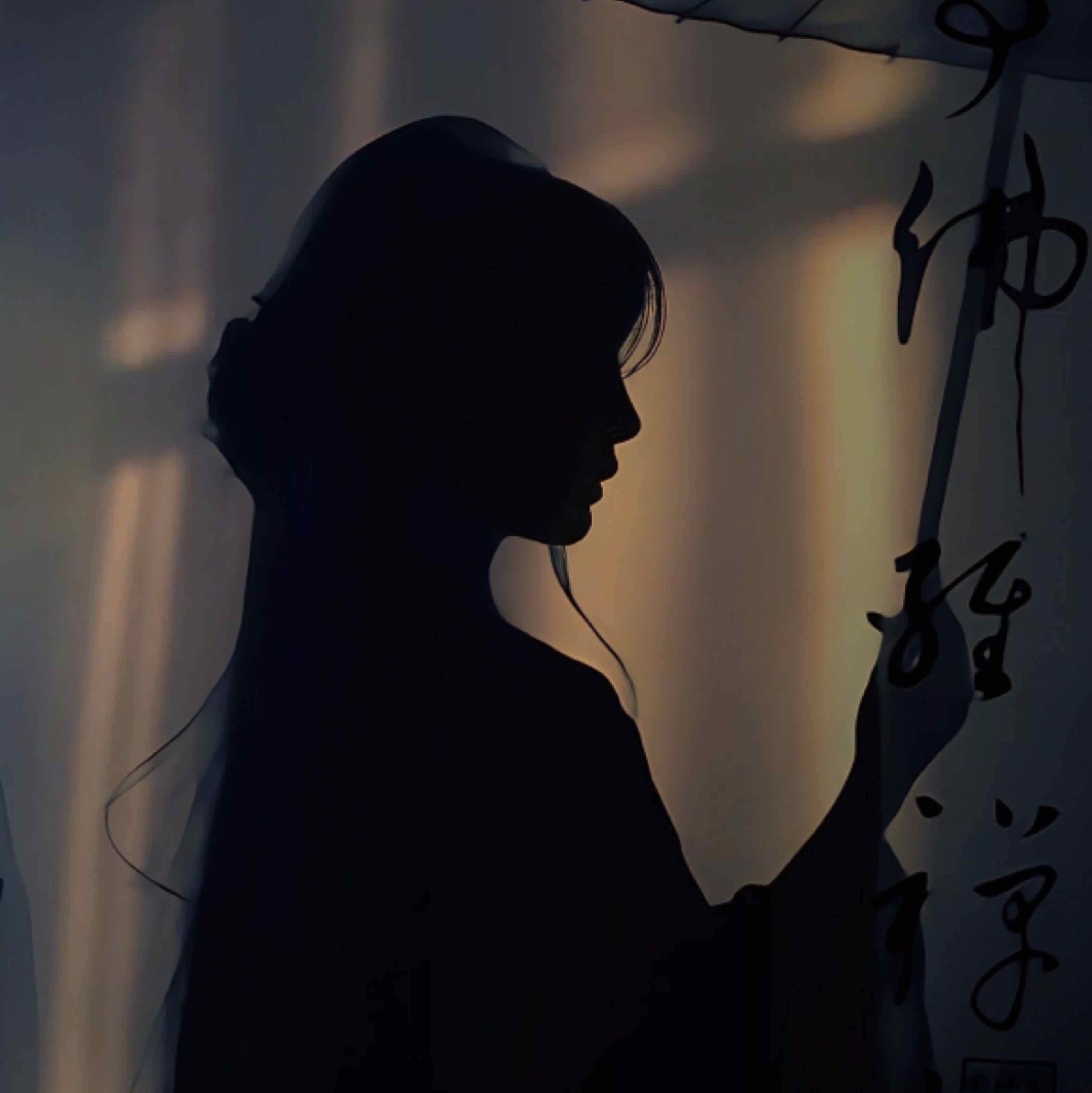
顧九洲
感謝寶子一個清冷的午后H的月票~
入夜,,城隍廟,。
謝昭打從進入城隍廟便像只趴了窩的鵪鶉,,她找到了一個相對干爽潔凈的角落,,然后便靠著柱子半點沒有講究的坐下,旋即整個人窩著蜷縮在裹緊的大氅中,,帶著氅帽一動不動,。
凌或是行動派,話少但是能干,。
其實方才路上他便已然發(fā)現(xiàn)與薄熄共乘一騎的謝昭像只蔫吧缺水的狗尾巴花似得,,老實安靜的可疑。
此時見狀更是不難聯(lián)想到她必是因先前在林中動過手,,導(dǎo)致那身舊傷舊毒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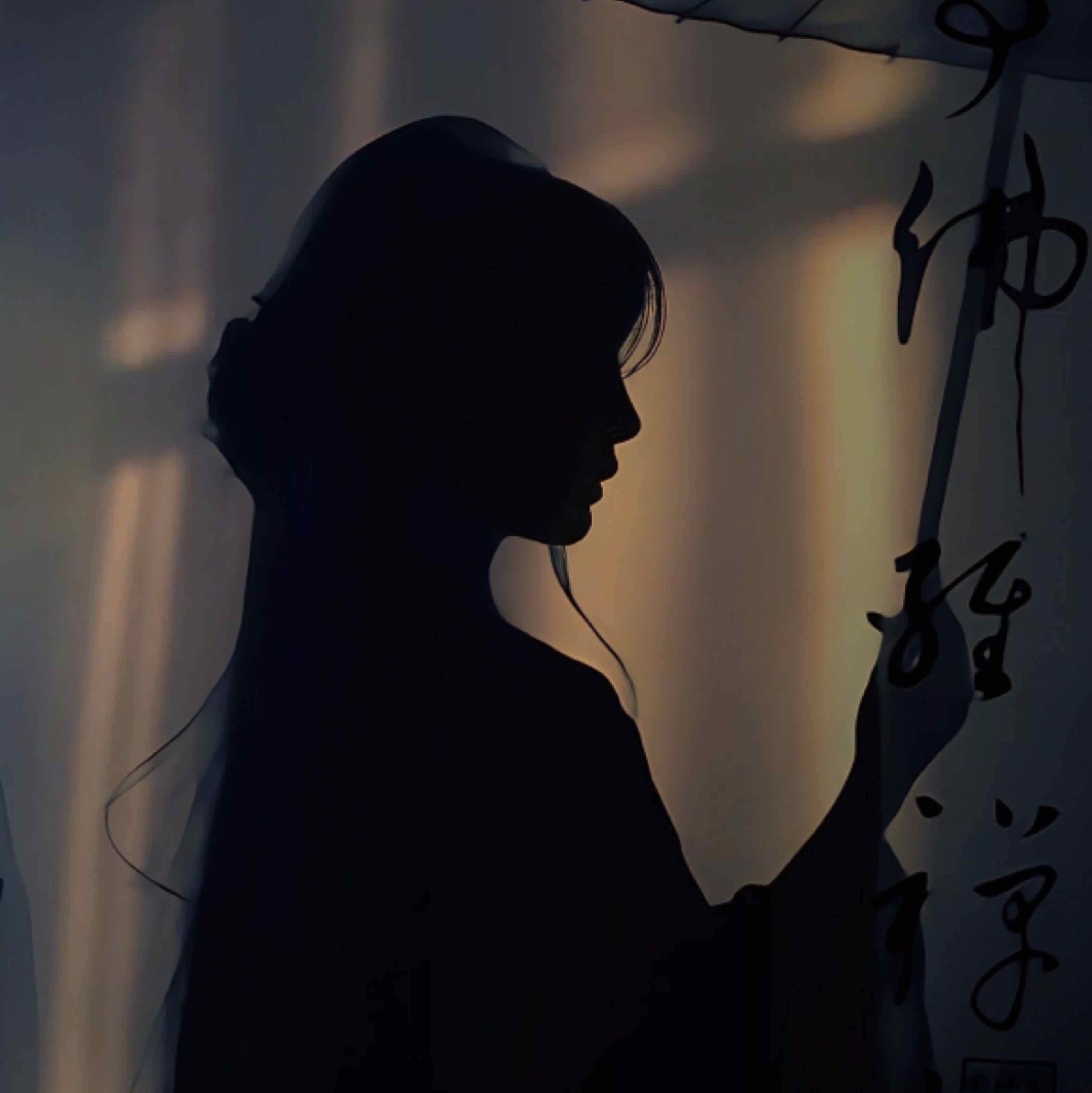
感謝寶子一個清冷的午后H的月票~